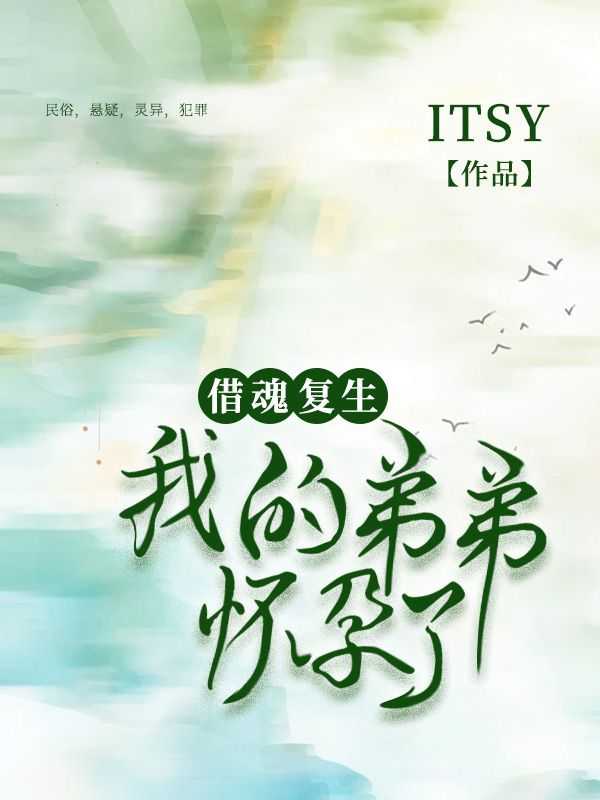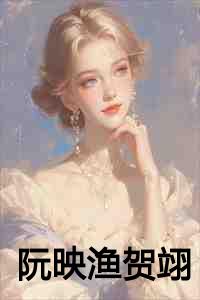车驶进酒店,黎筝跟着贺砚庭上楼。
行政套房在33楼,顶层。
贺砚庭挨着落地窗坐下,手指有一搭无一搭地轻叩桌沿。
也叩在黎筝的心上。
独处的时候,他是若无其事的,不自在的是她。
男人在这方面,确实比女人开放。
“司机买了豆浆,你洗完澡出来喝。”
房间静谧得落针可闻。
微妙至极。
贺砚庭审视了她好半晌,室温越来越高,他解了领带随手一扔,“去洗。”
黎筝跑进浴室,反锁了门。
脚底有些发飘。
和贺砚庭之间萦绕着一股剪不断理还乱的气氛。
不小心捅破,会一发不可收拾。
黎筝将保暖衣挂在门把手,拧开淋浴,发现没带浴巾,她重新开门出去,“你车里有毛巾吗——”
贺砚庭抬头,四目相对,黎筝才意识到他在通电话。
“你和女人在一起?”贺夫人耳力灵敏。
“嗯。”
逮了个正着,他没否认。
他身边没有女下属,包括工作助理和生活秘书都是男的,贺夫人也知情。
女下属相处久了,难保生出上位的心思。
一旦冒险朝他下手,目标势必是一步登天,母凭子贵当贺太太,不单单是几个钱了。
电话那端静默了一会儿,“你在什么地方?”
“酒店。”
“没回自己家?”
“没有。”
“你还算有分寸。”
贺夫人倒是有心理准备。
他忙于公务清心寡欲,毕竟是血气方刚的岁数,偶尔有一两晚忘情,也正常。
“什么职业?”
贺砚庭长腿交叠,抚了抚裤线的折痕,“女学生。”
黎筝吓得屏住呼吸,生怕贺夫人再听到一丁点她的声音。
“成年了吗?”
“二十。”
贺夫人在商场里,有美妆广告的广播,很嘈杂,“那姑娘已经同意见面了。”
“您安排日子。”
贺砚庭的态度既不期待,亦不反感,一切水到渠成,平和接受。
贺夫人略加思索,“安排在两天后呢?”
他仍旧嗯。
“那你要注意分寸了。”贺夫人不愿节外生枝,“该给女学生的补偿,宁可多给,别少给,最忌讳纠缠,你马上两清,从此断了。”
贺砚庭平静挂了电话,望向黎筝,“在床上的密封袋里。”
怪不得他从后备箱拎了一个袋子,原来是装毛巾的。
挺周到。
会照顾女人,体贴不滥情,要财有财,要型有型,没有哪个女人不爱。
“酒店的用品不卫生。”贺砚庭眼神意味不明停留在她身上,“你得病了,我也遭殃。”
黎筝耳朵嗡嗡作响,短暂的失聪了。
贺砚庭的意思很明显了。
只要时机合适,彼此都有感觉,他不排斥这段危险禁忌的关系。
“见面的日子定了吗?”
“定了。”
黎筝摩挲着密封袋的拉链,眼前浮现出那姑娘姣好风情的面庞,“你喜欢漂亮的?”
“不然呢。”贺砚庭转动手机,屏幕在拇指的反复触碰下忽明忽暗,“你喜欢丑的吗。”
力气大了,拉链崩开,合不拢了。
她捂住歪歪扭扭的拉锁。
“漂亮重要,不是最重要。”贺砚庭倚着沙发。
黎筝垂下胳膊,“家世最重要。”
“你这样认为的?”
她身体微微侧过去。
贺砚庭逆着落地窗的阳光,纱帘也挡住了光亮,他眉目神秘黯淡。
黎筝步伐很轻进浴室。
......
贺砚庭批阅完最后一摞文件,仰起头活泛着肩颈。
余光不经意一瞥,黎筝披着长发,在晾毛巾。
细白修长的脚脖子淤青褪去,戴着小铃铛的脚链,像他爱吃的嫩春笋尖。
他印象这铃铛的节奏感很好,尤其是她双腿架在他肩膀,一下接一下,他撞她,铃铛撞他,他狠,铃铛也狠。
配合他颠得乱颤。
简直是无言的诱惑。
贺砚庭站起来,脱了衬衣,锁骨处泛起一片动情的红。
他背过身,脊骨剧烈波动,连同皮带搁在沙发上。
浴室响起急促的水声。
水流开到最大。
黎筝翻着酒店的环球旅游杂志打发时间。
“毛巾。”贺砚庭叫她。
她走近一些,“没有新的毛巾了。”
花洒声很冲,冲淡了男人的音量,“你用过的那条。”
像是紧绷的一根弦,她不受控制地一抖。
“黎筝?”贺砚庭又叫。
她攥住衣架上湿漉漉的毛巾,门推开三分之一,水雾扑面,贺砚庭伸出手,水痕沿着他劲瘦的臂弯线条慢慢流下。
抓住毛巾,也顺势抓住她。
和在车里帮她取暖握手的含义不一样,现在他是男人,她是女人。
一个赤裸着,温度滚烫的男人。
她缩回手,背在身后。
隔着半透明的磨砂门,贺砚庭臀胯的轮廓雄浑自然的凸起。
“拖鞋。”
黎筝去门口,拆了一双新的拖鞋递给他。
室内蒸气熏腾,闷得她要缺氧了。
“还需要什么吗?”
贺砚庭接过鞋,“不需要。”
黎筝如释重负逃离。
十分钟后,司机买回来早餐,又交给她一个正方形的纸盒,“是贺总工的。”
她原封不动放在那一摞批完的文件上面。
司机前脚离开,贺砚庭敞开门缝,“小杨,给我。”
黎筝捧着一杯甜豆浆,“司机走了,你要什么?”
浴室没有了水声,传来的字字清晰,“有盒子吗。”
“有。”
“我要。”
盒子的标签扫过手腕,黎筝本能去看,男士纯棉抗菌裆内裤。
一条三角的,一条四角的。
她内心复杂。
贺砚庭气质肃穆正经,也有不为人知的,欲的一面,野的一面。
他的尺寸不适合三角裤,包不住。
起反应了之后,四角裤都差点撑破。
贺砚庭穿好裤子,擦拭着发梢走出浴室,“你在想什么。”
黎筝有一种被识破的尴尬,“想昨天考试的答案。”
“撒谎。”贺砚庭的眼睛如同一个钩子,深邃莫测,直勾勾的。
勾得她心潮起伏。
“司机买错了,我没穿过那个。”
黎筝低头,不搭腔。
“太窄,会漏。”
他拿热毛巾敷脸,舒缓精神。
这条毛巾她洗澡时擦过隐私部位。
贺砚庭埋在毛巾里的样子,她联想到另外一幕,臊得面红耳赤。
“你...”她欲言又止。
“你喜欢?”贺砚庭打断。
黎筝一怔。
“见过男人穿吗。”
她摇头,又点头。
“在哪见过。”
灯光柔和,照射得贺砚庭也比往日温柔许多。
黎筝如实说,“游泳馆。”
贺砚庭捏住她一缕长发,捋到耳后,她整张面孔完全在灯下。
“会游吗?”
她这次实实在在摇头,“没学会。”
“我教你。”贺砚庭似有若无地触摸她耳垂,他指腹有茧子,不薄不厚,糙糙的,是长期工作磨砺出的。
他抚摸过的每一寸肌肤,极度的敏感。
黎筝一颗心好似要窜出喉咙了。
片刻,贺砚庭摊开掌心,是一枚小小的珍珠卡子。
“太马虎。”
她洗头发忘了取下卡子了,揉来揉去和发丝搅绕住。
还浑然不觉。
“谢谢。”
黎筝卡住碎发,小珍珠精致圆润,她额头也小,贺砚庭又看了一眼她脚上的铃铛链儿,腰椎蓦地酥麻了下。
他眼底一阵暗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