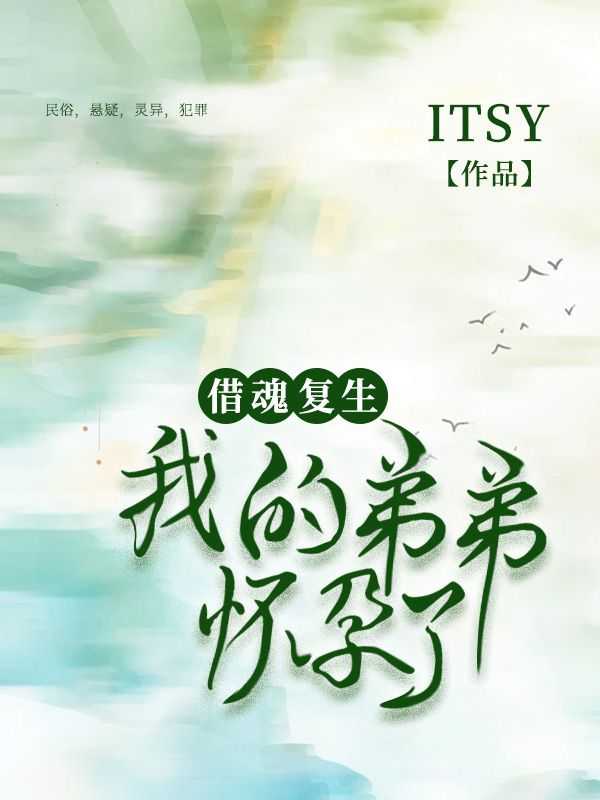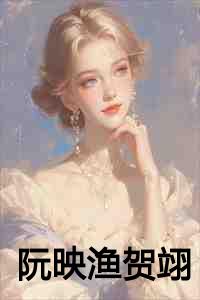偌大的院子里,气氛诡谲压抑。
我嗅着满院鲜血以及黄皮子的膻骚味,胃里一阵翻江倒海。
我能感觉到,我爸抱着我的身子,不住颤抖着。
这时,队伍里走出一只黄皮子,它来到陈邱设下的法坛前。
与其他黄皮子不同的是,这只黄皮子的头上,顶着一撮白毛。
白毛跳上了桌,从香炉里拔出三根正在燃烧的香。
接着,它转过身,学着人烧香拜佛时的模样,朝着院门外,恭敬地鞠了三躬!
院外漆黑一片,什么都看不见,可这群黄皮子的举动,给我一种感觉。
就仿佛黑暗中,正有着什么东西,窥视着一切!
半晌过后,白毛似乎得到了回应,将香又插回了香炉。
转而扭过头,极具人性化地冲着我爸招了招手。
它做这个动作的时候,活灵活现,那模样,哪怕它下一秒就口吐人言,我都不会觉得奇怪。
与此同时,围在我爸四周的黄皮子,也都让开了一条道。
眼下,就连陈邱都倒了,我爸就是想不过去,都不行。
他抱着我,小心翼翼地接近了那只白毛。
当距离对方不过半米左右的时候。
白毛忽地一蹬腿,跳到了我的身上。
我爸吓得抬手就要将它拍开,却为时已晚。
白毛张开嘴,对准了我的左手,吭哧就是一口!
顿时,我只感到钻心的疼,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。
我爸见状,怒火一下子涌上头顶。
他也顾不得四周都是黄皮子,抓起那只白毛,将它用力摔到了地上。
白毛吱吱叫着跑开,嘴里,始终叼着我右手的半截食指。
“你个畜生!把我儿的手指还过来!”我爸怒吼着,就要冲过去。
也就在这时,院外,由远及近,亮起了一片火光。
村长大喊着,举着火把,带着村民们又杀了回来。
白毛见状,连忙领着黄皮子,顺着我家后院,消失在了山林之中。
等村长到时,只看到躺在地上,奄奄一息的陈邱,还有抱着我,泪流满面的我爸。
至于我,早就疼得昏死了过去。
等我醒来,已经是第二天早上。
我躺在县医院的病床上,左手被包成了粽子。
村长就坐在我身边,我张口的第一句话,就是问我爸去了哪里。
村长叹了口气,神色哀伤:“上山请罪去了。”
“啊?”我没太听明白。
“伏牛山,陈道长他已经......”
村长语塞,没再说下去,但我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。
陈邱陈道长,死了!
得知陈邱的死讯,我心情瞬间跌落到了谷底。
在我看来,他的死,都是因我而起,是我害死了他。
小小年纪,正是多愁善感的阶段,我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。
村长见状,忙安慰我,可我根本就听不进去。
这会,一名小护士推门进来,将村长叫走。
村长前脚刚走,后脚,病房门就被人推开。
我以为是村长回来了,抬眼看去,却见来人并非村长。
那是一个陌生人,准确来说,我连他是男是女,都分辨不清。
发生这件事的时候,还是秋分的季节,天气很热。
来人却穿着一件连帽的大衣,整个人裹得严严实实的,脸上还戴着口罩和墨镜。
唯一露在外面的,是那一双手,很白,很嫩,像是城里姑娘才会拥有的手。
那人三两步来到我面前,伸出手,在我脸颊轻抚,指尖还带着微微的颤抖。
我害怕极了,换做是谁,被一个陌生人这样子摸脸,都得害怕。
我抵触地将身子往后缩去,弱弱地问道:“你......你是谁?”
听到我的话,那人的手顿时僵住,接着,颤抖地吐出两个字。
“孩子......”
简单的两个字,却勾起了我无限的遐想。
这是一个女人的声音,很慈祥,很温柔。
一个在我心中,走丢了十二年的人,跃然于心。
我瞪大了双眼,就在我即将开口之时,村长回来了。
他看到病房里多出的陌生人,面色当即一冷:“你谁啊?”
女人浑身一震,将口袋里的东西往我被褥里一塞,转身便走。
村长伸手就要去拦,却被女人猛地一把推倒在地。
等村长爬起来,追到门口的时候,女人已经跑没了影。
村长骂骂咧咧地回屋,问我道:“小杨,刚刚那人谁啊?你认识?”
我摇了摇头,什么都没说,手里死死攥着女人塞给我的东西。
那是一块拇指大小的玉石,通体冰凉,晶莹剔透。
在玉石中央,有着一抹红色,很浅,像是一道裂纹。
这天,是我和我妈,这辈子的第一次相遇。
过程很短,但我能感觉得到,她并不像村里人说的那样,是个将我们父子抛弃的无情无义之人。
村长见我不说,便也没再深究,而是告诉我,下午的时候,白眉道长会亲自出面,替我破解身上的冤煞。
白眉道长,也就是陈邱的师父,他并没有责怪我爸,而是说,昨晚的一切,都是陈邱的命数。
他命中该有此劫,谁都拦不住,但那群黄仙害死了他心爱的徒弟,他必须报仇雪恨。
于是,当天下午,村长就将我后续的治疗,转去了村里的小诊所。
到家时,已经是下午两点,白眉道长正在院中,捧着爷爷留下的那个木盒,仔细端详。
他大概五十来岁年纪,穿着一件白色长袍,人如其名,两条眉毛雪白。
按理说,像这样的高人,都会给人一种道骨仙风的感觉。
可眼前的白眉道长,双目狭长,看着更像一名该被吊路灯的资本家。
见我回来,白眉道长放下了手中木盒,替我检查了下手上的印子。
接着,他问了我一个问题:“小家伙,你是不是不会水啊?”
说来真巧了,我们村名叫河子村,村东头有条百丈宽的大河。
照理说,像我们这样的穷乡僻壤,都是靠山吃山,靠水吃水。
我们村的孩子,大多三五岁,都能下河捞鱼了。
偏偏我是个特例,我不会游泳。
甚至,对于水,有着一股莫名的抗拒。
“嗯。”我点点头。
白眉道长笑着回头,看了我爸一眼。
“没错,娃娃是天生的弱水命。”
“也难怪,三爷会拿地婚借寿这么毒的法子,来给他续命!”